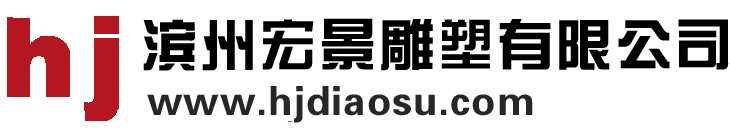不久于人世的雕塑师在一个将尽的夏夜向梦中的亚当借了一块雕石。第二天,他抽出整个清晨和午后思考(或回忆)美的全部可能性,尽管石头的主人曾慷慨承诺,无论这块石头最终雕成什么,都将意味着永恒。雕塑师对着这伊甸园的礼物凝视了太久,他见过马尔塔时代的七色珐琅矿石,见过连沙兰西国王都不曾收藏有的绝世美玉,在他年轻的时候,还用印第安某个山林部族的祭献品(那是颗散发淡青色月光的珠石)雕刻了一枚胸章。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一块雕石,外表没有颜色,甚至没有外表。有种奇妙的触觉和冰凉的质感,当雕塑师把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时,就像捧着一个宇宙。
日积月累的惯性推动着雕塑师的思考,他始终相信永恒意味着形式和过程,意味着思考本身,而非完成的作品。于是又一个黄昏过去了,除了徘徊,没有人看见雕塑师挪动半步。他就像一个忏悔者,在教堂逐渐暗淡的光线下锲而不舍地与不见脸孔的神父交谈。雕塑师拿起石锥,在这块坚硬的宇宙上凿了凿,迸溅的碎屑如同闪现的灵感,他突然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。他朝窗户点点头,一只乌鸦飞走了,棕色的树枝微微颤动。
雕塑师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,世上还没人这么干过。他早已忘了激动的滋味,而此刻他那颗年轻而敏感的心复活了,他紧握着石锥,就像魔术师紧握着手中的白鸽。他要在一个奇迹上创造另一个奇迹,他深知艺术开端的艰难,所以当他在石面上雕琢着第二条沟壑时,已是黑夜。他捏出最后一根火柴,点燃最后一支蜡烛。工作必须在黎明前完成,他已能听到窗棂上黑色翅膀的响声。
有几只幽灵从墙缝里钻了进来,它们生前都是老实人,此刻它们聚集在门边,窃窃私语。最矮的那只幽灵说,雕塑师在雕塑一只动物,是埃及的灵狐或胡狼。最胖那只的幽灵说,雕塑师在雕塑一块面包,是硬草莓馅的。最高的幽灵摇了摇尖脑袋,他说,雕塑师在雕塑一颗星球,但肯定不是地球。吵闹愈发激烈,甚至有一个声音宣称,雕塑师在雕塑一座天堂。它们坚持己见,丝毫不让半步。它们扭打起来,像一幅扑克在自动洗牌,不断有古怪的面孔从那一团混乱的白色中弹出。
深夜时分,雕塑师已完成了最艰难的部分,条条精致的沟壑如同起伏交错的山脉,一只幽灵甚至恍惚看到有水在其间流动。到了黎明前,所有在场者都能清楚的看到,匍匐在雕塑师渐渐摊开的双臂前的既不是动物也不是面包,既不是星球也不是天堂,而是颗跳动的大脑。
光秃秃的雕石上忽然睁开了一双眼睛;忽然伸出了一对耳朵;忽然吐出了一张嘴(这张嘴在吐出的同时顺道把蜡烛吹灭了)。幽灵们又议论纷纷,最矮的幽灵说,那一定是雕塑师的前妻,因为她曾因雕塑师的古怪个性弃他而去。最胖的幽灵说,那一定是雕塑师孩子,因为没有孩子,他一身技艺无从延续。最高的幽灵摇了摇尖脑袋,他说,那一定是雕塑师的朋友,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,友谊也已足够。
这回幽灵们猜对了。如果黄昏时亚当从永恒之梦中探出脑袋,就会看见雕塑师最初的思考内容。他不是没怀念过那些踩在落叶上的日子,那些仍与世界存在种种交集的快乐的日子。事实上,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前妻。他的眼睛融化了,胸中升起的热雾使他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。他望着那块雕石,直到上边显现出一张女人的脸。但他随即明白,雕塑大脑和雕塑记忆是两回事。他低下头,嘴上露出嘲笑。他不是没想过造一个孩子,他多么苍老,却从未享受过天伦之乐。他常常看见人们对孩子施加着错误的教育,他总想,要是自己也有孩子就好了,那么他就能从一颗纯洁无暇的心灵那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和灵感。但他很快就被这自私的想法吓住了,他回过神来,回到现实,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要如何肩负抚养的责任呢?他只剩下一个选择了,他回想在生命的旷野里自己最期待的是什么,他尝够了孤独,尽管他认为孤独对自己有好处。如果说世间存在最伟大的艺术,他暗自思忖,那便是友谊了,又有什么幸福能比得上两颗同等深度的心灵的相遇呢?于是,他决定为自己造一个朋友,一个能理解他所有孤独的朋友,一个同样孤独的探索者。
云层破了一个洞,一束天光射下来,像照亮一口井那样照亮了世界,照亮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黎明。雕塑师将他的新朋友搬上窗台,借着晦涩的光亮,看清了对方的面孔。那是一张他在镜子里反复见过的脸,是他自己。雕塑师大限已到,他来不及露出遗憾的微笑就死了。这时,那束一视同仁的天光越过远方的山脉,也照亮了这两位雕塑师。就这样,他安静地死了,一道投影从窗台上缓缓映下来,映在他身上,像时针重叠在分针里。
;说说您的看法:(无须注册)
共0条评论暂没有评论。